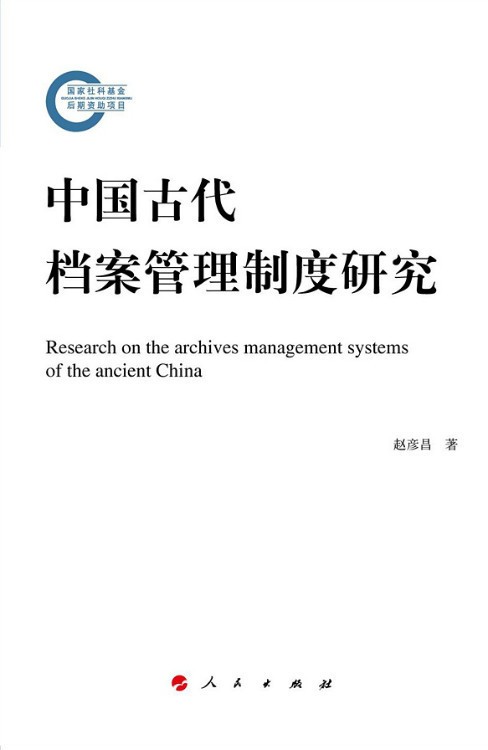凸现《档案春秋》选题策划的记忆功能----以“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专稿”操作实务为例
2012/3/16 点击数:1438
[作者] 架阁郎
[单位] 兰台天地II
[摘要] 档案春秋》作为一本档案人文类的综合性文化期刊,表达和传递档案中所荷载的历史记忆,是这本杂志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然而,没有对现实的敏感,就不会有对历史的贯通。所以,从2005年创办之初,我们就把近现代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专门列了一张表,张贴于案头,时时提醒身置于当今语境的自己不要忘记,以便及时作出反应,尽早进行选题策划、稿源组织和作者遴选。
姜龙飞
档案春秋》作为一本档案人文类的综合性文化期刊,表达和传递档案中所荷载的历史记忆,是这本杂志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然而,没有对现实的敏感,就不会有对历史的贯通。所以,从2005年创办之初,我们就把近现代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专门列了一张表,张贴于案头,时时提醒身置于当今语境的自己不要忘记,以便及时作出反应,尽早进行选题策划、稿源组织和作者遴选。
对于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暨国庆60周年的选题策划,早在2008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着手了。当时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奥运狂欢中,没有谁来要求我们这样做,编辑实践也证明做专题远比做非专题的自由混搭困难得多,但出于职业敏感,我们还是做了,时不时的在脑子过一过想一想。这似乎已经成了档案专业工作者的一种习惯,或者说宿命,好像记忆就是我们的本能,没有多少宏大的理由,几辈辈档案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被动的职业习惯,但换一个角度理解,表达和传递档案中所荷载的历史记忆,又何尝不是《档案春秋》文化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完全可以、也应当变被动化为主动。“档案”这个字眼,在长期形成的社会属性中,不仅给人以隐匿、隔膜的神秘感,让人敬而远之,更具有真实可靠的天然禀赋,享有很高的公信力。用一句官方语言表述,档案所负载的,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使命。在以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万马齐喑的某些时候,因为封闭,档案得以独善其身,长期钳口,虽然被阻断了开放管道,但也极大地避免了说胡话的风险;宁可存史,绝不佞史。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后的近30年来,我们仍然难以摆脱幽闭的历史阴影,悟性开化迟钝,对档案的理解偏于狭隘,操作方式流于机械,传播形式失之概念,完全忽略了档案信息还兼有多重价值取向。除了崇论闳议、铁画银钩,还有持平公允、直谅多闻的一面,不易随风赋形、热胀冷缩,质量比较稳定,褒贬基本可靠;而作为公共读物,在大多数时候,档案叙事给我们的审美快感,应当集中在拼图般的探赜索隐和茅塞顿开的真相还原上,以亲历、亲见、亲闻取胜,或以如同亲历、亲见、亲闻般的模拟复制引人入胜。搜索、剪切、粘贴;细节、氛围、文笔,是支持这一切的重要的技术手段。经审美之火熔炼的记忆重现,辅之以直击感强烈的图像、实物,可以极大地满足阅读者对历史内幕的探究欲。正如古罗马哲人西赛罗所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相信没有谁愿意永远做幼童。
只有把上述文化品格和审美要素配置齐全了,至少调配得大体到位了,档案才有望摆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卜算子·咏梅》)的枯涩,逐渐复苏其与公众的亲和力。私心忖度,我们似乎还应该有意识地保留一点档案的神秘感,悬念永远是最大的看点。如此,《档案春秋》方能凝聚起自成一格的竞争之核,“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辛弃疾《山园小梅二首》)
纪念重大节庆,说好做也好做,毕竟多年来积累的档案史料已经叠床架屋,随便挑出一些来,应付一下绝无问题,而且图文并茂。但说不好做,也的确困难得很,上海解放已经整整60年了,60年来哪一年不得就此选题下一番功夫,从党委宣传部门到档案界到各大媒体到出版单位;从1年庆做到10年庆、从10年庆做到20年、30年庆……各个重大的历史节点,我们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眸再回眸,可用的、凡不涉及机密的档案史料已悉数亮相,基本上穷尽了,再想翻出点新意来,难乎其难,有时简直给人走投无路之感。
从一开始着手策划,我们就陷入了惯常思维的窠臼。
反复掂量权衡,脑筋绞得简直要滴下水来,最后很无奈地定下一条:老的档案史料,老的思维角度,肯定都还是要用的,但怎么用出新意来,用得能让读者看得下去,读得津津有味,不厌弃你“炒冷饭”,可能是比翻检新史料更为现实的一条路径。但老材料和新做法完全可以齐头并进、双管齐下。
从去年秋天开始,我们先着手翻检档案史料,从市档案馆,到若干个区档案馆,我们都去了,找了。今年年初,我们的上级领导机关,上海市档案局、馆为编辑出版上海解放专题档案史料,专门组团前往北京,去向中央档案馆和解放军档案馆求援,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一些和解放上海相关的新的档案史料。《档案春秋》也派人随团出发了,不仅去了上述两家档案馆,我们的编辑还去了外交部档案馆,那是一家近年来档案开放力度轰动国内外的档案馆,甚至成为了表征中国政治清明、信息开放的标志。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从台湾获取档案史料的渠道,不然也值得一试。
几番辛苦,收效不大。但,即便点滴所得,在我们也是得来不易啊!
新史料不足,还须借新做法适当补拙。借鉴近年来电视媒体“重走××路”的操作模式,作为平面纸媒,我们不妨也学学人家的创意,决定重走一遍解放上海之路:以江苏丹阳为起点,重温当年解放大军沿沪宁、沪杭两路东进,一路摧枯拉朽,最终拿下大上海的辉煌历程。回顾近年来的宣传报道,笔墨大量集中在市郊和市内作战,但事实上上海之役从1949年5月初邓小平、陈毅、粟裕等率领总前委入驻丹阳就开始了,这其中的过程很多人还不太清楚,很有文章可作。
二
我们的策划得到了局党组的大力支持。近年来我们的每一次策划,例如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等纪念专稿的编辑出版,都从市档案局主要领导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从精神到物质,实在是幸运之至。档案的开放与传播,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还是一种政治行为,关乎政府信息开放和政治民主化建设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所以,是否严格恪守党和政府有关新闻出版的各项政策规定,准确执行有关档案开放的法律法规,确保政治正确,是市档案局领导一直关心的核心问题。此外,对于一些敏感话题,诸如防止片面追求猎奇、揭密,审慎地对待曝光、解禁,杜绝泄漏档案中涉及的个人隐私等,也在局领导们经常性的微观之列。我们的编委会主任,一直由局党组书记、局长兼任,我们的主编,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分管副局长担纲;每一期杂志,从选题策划,到每一篇文章、每一帧图片,都在他们的直接审视下定夺,可谓殚精竭虑。
《档案春秋》关于“重走上海解放之路”的选题策划,经组织程序汇报到市委宣传部,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市委宣传部甚至要求本市主要新闻媒体一同参与此事。
今年3月,我们“重走上海解放之路”的采访启动,但因为前述放大效应,此事已经变得不再是《档案春秋》的独家行为了,而上升为组合套路。行前,先由上海市档案局行文江苏省档案局,再由江苏省档案局下达通知到丹阳、镇江、常州、苏州、太仓等诸多市县档案局,要求给上海的同志以配合。原本只是我们杂志自选的采访,也变成了兼负为电视台踩点、选秀(采访对象)、定线(采访路线)的规定动作;领队的规格也骤然从我这个一介布衣让位给了市档案局副局长,江苏的同行一路迎来送往,真是搞大了。领导重视是好事,但这也恰恰反证了多年来反复做一个相同的重大选题难度有多大,只要稍见亮点大家便一齐来劲。
位于丹阳的总前委纪念馆的确是值得一去的重镇、宝地,因为几十万大军挥戈东进的主要决策、命令,大多在这里形成和发出,接管上海的5000干部也在这里集中和培训。其貌不扬的这座二层小楼,是60年前决定大上海命运的大脑和中枢。还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对这家纪念馆的维持竟然是由一个叫贾云飞的中年汉子自掏腰包完成的。尽管据说贾馆长做生意很成功,很有钱,但能够拿出私房钱来行此公干,还真有点义薄云天的风骨,让我肃然起敬。有机会《档案春秋》一定为老贾作一篇文章,让大家看一眼物欲横流的当下也有真汉子。
陈毅当年曾在丹阳对南下干部作过一次讲话,很是著名,其录音至今仍存于上海市档案馆,然而寻找可以见证这段讲话的大王庙广场却颇费周折。我们在丹阳小城的曲径幽巷中绕过来拐过去,从日照当头一直找到夕阳将尽,结果大王庙是彻底找不到了,原来恭请大王盘踞的庙宇现在变成了幼儿园。孩子才是我们世世代代永远的王。天色将晏,幼儿园已经人去园空,孩子们都回家了,只有院子里靠东墙的一侧,简简单单地立着一块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小字:陈毅对接管上海市干部进行入城纪律教育旧址。不趋近了看,暮霭之中难辨真切。一阵小风刮过,冠盖于石碑后侧的一株高大的蒲葵树微微摆动,像一位历史的倾听者,对陈老总当年的声音凝神颔首:“上海城市工作中的困难,第一是管理指挥600万老百姓,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张大口又要饭吃,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和生活问题,单是每天的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进城后要虚心谨慎,要小心,我们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战上海不出5月,或者就是近几天后的事!”……
三
今年5月上旬,刊有“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专稿”的《档案春秋》终于如期出版,专稿汇集了我们苦心经营了大半年的13篇文章,品种杂沓,有通讯、口述、回忆录、档案公布、旧文新读、报告文学等七八种样式,图文并茂,黑白加彩色参差有致;人文色彩浓郁,形成了一种具有生命形式的结构系统。后面几期杂志,我们还将有同题稿件陆续推出。
注重刊物内容的丰富性、人文性和可读性,是我们从创刊之初就特别在意的一件事。这种自觉意识也贯穿在了“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专稿”的选题策划中。得专业便利之所长,先天具有档案信息集散和流通的优先话语权,是《档案春秋》区别于其他人文历史类期刊的突出优势,只不过这种优势在过往的岁月里因为缺少相应的操作平台和实施手段,而被世人、也被我们自己忽略了。紧紧扣住这一优势,使之渗透到我们的办刊理念和实际操作中,并通过每一期杂志、每一次策划,具体真实地凸现出来,既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与职业优势相得益彰的表达手段。千万不能太学究气、太自恋了。那种以为档案期刊必须靠史学研究来抬高身价的说法有妄自菲薄之嫌,虽然操作手段传统省力,但实践证明是缘木求鱼,难成正果,最终迷失的将是深度的自我。人的记忆何其丰富,何其传神,我们怎么能自设禁脔,自缚手脚,把档案圈定为个别人的专利,把历史公器变成同仁间自娱的工具?每一个拥有往事的人都拥有档案,每一个拥有档案的人都拥有历史,每一个拥有历史的人都拥有对历史的话语权。我们所理解的档案是广义的,不必以所谓“懂不懂”历史来划线,也不必囿于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专家写得,布衣写得,草根也写得。“掉书袋”者未必深刻,佶屈聱牙者大多浅薄,语言的流畅必然和思维的清晰互为因果。我们的读者更无须在乎有没有学术背景,草根读得,布衣读得,专家亦读得。关键在于我们刊发的文章,是否能还原一幕幕历史场景,重现一段段人生过程;是否能撞击你的心灵,激发你的共鸣。我们追求活的记忆。“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专稿”,或可体现我们的这种追求。
载有“专稿”的第5期杂志出版的第二天,编辑部就电话不断,一些老战士、老领导不仅5本10本地要求邮购,还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尽管我们德薄能鲜,自愧不如。对于这些身份特殊的读者,我们“不差钱”,一律慷慨相赠。本埠主要新闻媒体文摘版的编辑,也纷纷来电联系转载。截至5月底,已经有半数以上的专稿文章,被《新民晚报》、《文汇报》、《天天新报》等转载,转载时所占篇幅之大,转载时间之集中,均大大超乎我们的意料。顺便说一句,近年来《档案春秋》所刊文章的转载率一直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外省市报刊的转载数量难以准确统计),每年都在六七十、乃至八九十篇次,今年刚刚到5月底,已有45篇次的文章被转载,而我们每年的发稿总量也不过一百多篇。这说明了记忆实乃人的本能诉求之一,是一座与心灵同等广阔的经验平台。它不仅忠实地记录着历史,而且它的构建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它的书写和被书写,将随着生命的延续而延续。我们并不否认档案与方志、史学等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但若细分,却终究不是一回事,如果简单地、常规地把记忆和它们等同起来,恐怕不尽允当,实际操作也会有很大差异。档案应当更原始、更本真、更感性一些,大致做到通古今之变就可以了,究天人之际可以让给别人去做。借用西赛罗对戏剧的一个著名解释,我们也可以说,档案是“人生的一个复本,风俗的一面镜子,真理的一种反映”。这就是我们定位于档案人文和档案文化的由来,并谨慎地和史学类杂志错开身位,不想步人后尘,不搞同质竞争。
事实证明,我们的定位与操作是基本可行的,得到了有关主管部门和广大读者的认可。早在2007年,《档案春秋》就被纳入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百种优秀期刊进连队的名单,还被新闻出版总署认定为A级期刊。4年来,尽管我们的宣传经费严重不足,基本没有投入,人手极其有限,少有余力进行发行推广;在内容与营销之间,我们选择“内容为王”是出于无奈,但邮发量仍年年攀升,今年甚至出现了月月攀升的情况,尽管数量不大,却说明了读者的口口相传正在坊间发生作用,这是比数量再大的公费订阅都更令人欣慰的事。
原文连接:http://jiageku.blog.163.com/blog/static/126069173201221691441278/